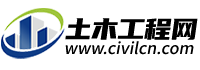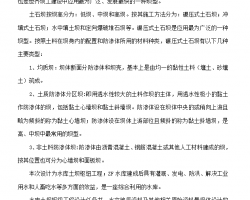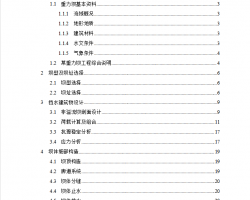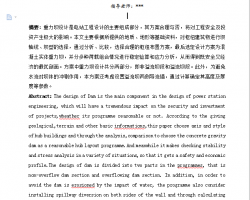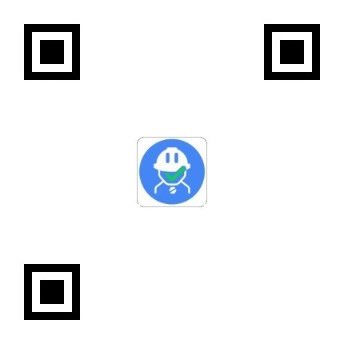摘要:利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中国的农村水环境治理问题。结果表明,农村水环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需要村民、企业、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但各主体在行动中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都出现了“搭便车”的行为。实现农村水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企业激励机制、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克服各治理主体的“搭便车”行为,增强主体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识和行动能力,实现农村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水环境;治理;集体行动;选择性激励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基础。农村水环境是中国江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大农民生活和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以及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随之产生的农村生活、生产污水以及企业排污现象严重危害了农村水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优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研究村民、企业、地方政府等治理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使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到农村水环境的治理行动中,对改善农村水环境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1 农村水污染治理的紧迫性
中国农村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根据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的点位中,I类、II类、III类占71%,劣V类占6.7%;七大流域内,辽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污染最为严重。地下水水质状况更加恶劣,在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中,I类、II类、III类水质仅占13.8%,IV类占70.7%,V类占比达到了15.5%,除了锰、铁、浊度、氯化物、“三氮”等指标超标外,部分点位铅、锌、砷、汞、六价铬等危害极大的重金属超标[1]。根据中国的水质标准,劣V类除了生态调节功能,并不能为人类所使用。在农村地区,由于水处理系统不完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大多直接使用地表水和地下水,严峻的水污染状况危害了农村地区人民的安全。据调查显示,农村约有2.27亿人口存在饮用水不安全问题[2],农村水环境治理刻不容缓。
2 集体行动的逻辑
传统的集体理论认为,一个组织(或者集团)中的成员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奥尔森[3]则以“理性经济人”假设贯穿他的理论,认为集团中的成员“显然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强烈的个人理性使个体成员更关注自己的收益,争取自身利益,在面对集体利益的时候,理性的个体不会积极参与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出现了集体行动中个体成员“搭便车”的现象。个体成员选择“搭便车”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集团中成员共同利益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集团的共同利益就具备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共同利益得到满足意味着向集团提供了一个公共产品,集团中的成员不论是否付出成本都能够分享收益。二是由于个人利益与集团利益在某些程度存在重叠,必然会有成员采取行动,当他们发现不参与集体行动的其他成员同样能享受收益,而自己支付的成本却高于收益,就会降低他们行动的动力,最终停止为获取共同利益而支付成本。个人理性的支配下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集体利益,与集团的规模有关。小集團中成员数量较少,个体成员通过集体行动获取的收益在集团总收益中的占比较大,个体成员收益高于支付的成本,因此小集团中的成员能够自发参与集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但小集团中也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大,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而增进集体利益所获得的收益减少,帕累托最优就越难实现。奥尔森通过对大集团和小集团中成员行动进行分析,得出了“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们的共同利益”[3]这一结论。 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奥尔森提出要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主要内容分为2个方面,一是奖励手段,通过提供积极诱因来引导集团成员的行为,奖励作为推动成员追求共同利益的诱因,对积极支付集体物品成本、参与组织目标实现行动的组织成员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其收益超过参与实现组织目标所支付的成本。二是惩罚手段,以强制性措施来刺激集团成员的行为,通过某些手段,增加成员“搭便车”的成本,以此来激励个体成员采取行动。“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经济手段,包括奖励性工资、福利等,也可以是声望、名誉等非经济手段。采用这种排他的激励方式,将在组织行动中采取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的人加以区分,做到赏罚分明。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将满足私人利益的动机转化为增进共同利益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改变集团中成员提供集体物品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解决集体行动中的不作为和“搭便车”行为,使集团内的成员都能够参与共同目标实现的行动。
3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困境研究
从农村水环境的性质上来看,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水环境治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其非竞争性体现在流域内的任何主体享受水环境优化带来好处的同时,都不会影响其他主体的消费;非排他性体现在流域内的所有主体都可以平等享受水环境治理后带来的收益,即使是不付费的成员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因此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视角来分析农村水环境治理,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村水环境治理带来的生态改善等效应是各个主体追寻的集体利益,但是由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共物品属性,村民、企业、政府等主体面对水环境破坏,处于观望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企图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获得利益,而不是积极履行自己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职责。
3.1 村民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村民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有着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农村水环境的受益者、破坏者,也是治理者、维护者。村民只有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农村水环境的重要性、水污染后果的严重性,积极保护、治理农村水环境,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才能有效推动农村水环境的改善。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村民群体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集团,在这个“大集团”中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所有人追求的共同利益。村民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寻求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选择,他们认为即使自己不参与水环境的治理,也可以从其他村民或者是政府和乡镇企业的环保行为中获得好处。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大多村民都存在“搭便车”的行为。根据黄森慰等[4]一项关于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参与意愿和参与度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村民中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水环境治理工作,可见村民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很少会采取行动。
村民在水环境治理中“搭便车”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村民作为农村水资源的直接受益者,依靠水源灌溉作物、维持生活的同时,产生大量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化肥农药农膜、人畜粪便。村民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采取牺牲生态利益而满足自己的利益,例如为了自身方便把村中的池塘、河流视为排污场所,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粪便等排入水体中;为降低耕作成本使用强效化肥,加剧了水体污染;为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支出,宁可破坏生态环境也不愿采取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行为都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大多数村民在面对农村水环境的破坏行为时,会选择忍气吞声,采取观望的态度,只要他人的行为不危及到自己的利益,便置之事外,任由破坏水环境的行为发展下去。这种“搭便车”的心态,加之知识水平、政治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村民对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识普遍不高,最终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败。
3.2 企业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企业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企业生产排污对农村的整体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的不断加强,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搬到农村。部分企业缺乏水环境保护意识和污水处理设备,或企业从利益出发,工业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农村的池塘河道中,严重污染农村的水环境,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企业的生产排污是农村水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作为农村水环境的破坏者应当承担农村水环境治理的责任。但是,实际上企业很少主动参与到农村水环境的治理中,往往也会选择“搭便车”。首先,生产活动造成的水环境污染负外部效应并不由其单独承担,而是由与其处在同一个水环境的主体共同承担,企业无需为自己的行为单独付费,并且水污染对其造成的损失远远低于为其创造的利润。其次,企业作为追求利润的“经济人”,其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污水处理设备与技术的引入费用高昂,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更愿意采取隐瞒污染情况、经济补偿村民或寻租相关政府等方式避免检查,也不会增加成本引入先进设备或技术进行水环境保护”[5],特别是乡镇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设备简单,加之环保意识薄弱,更加不愿在水环境保护中投入大量成本。同时,“搭便车”的心态使企业认为,即使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其他企业不采取行动,自己的环保行为也是无用之功,农村水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企业的“搭便车”心态使其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动力,加剧农村水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制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地方政府在農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对农村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保护负有主要责任。运用政策性手段治理、规范各类水污染行为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政府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可以看作是“理性经济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以及政府官员个人显然拥有独特的利益偏好,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在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自利性”行为难以避免。 在“理性经济人”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为满足其利益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不仅难以履行农村水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职能,反而在某些程度上成为农村水环境恶化的“帮凶”。首先,行政权力下放、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营利空间,同时以GDP为主要标准之一的政绩考核指标形成了地方政府压力体制[6]。在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个人政绩的诱惑下,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甚至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忽略社会责任和民生发展,对于那些高污染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视而不见,企图通过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以实现个人的政绩目标,而对那些环境友好却收益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企业缺乏发展的热情。其次,地方政府的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权力被分割、职能被分散,水污染治理涉及环保、水利、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缺乏统一的农村水污染治理部门或权力协调机制,部门之间职权分割不明,出现了“群龙治水”的现象。面对水环境污染问题,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利益难以协调,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扯皮推诿,互相观望彼此的行动,企图通过“搭便车”的方式逃避职责[7]。中国政府最基层的环保部门仅仅到县级,乡(镇)、村未设立直接的环保机构,这就使环境治理与监督在乡(镇)、村两级出现了真空现象,县一级环保机构难以实现有效监管,面对庞杂的基层水环境监督和治理任务,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特别是在面对企业和农民的水环境冲突的时候,基层政府为逃避履行职能,利用农村的熟人社会,常常采取“和稀泥”的方式,而不按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企业采取处罚,更纵容了企业水环境污染行为。地方政府在农村水环境污染中的“搭便车”行为致使其在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中无法发挥其职能,导致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主体缺位。
4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困境对策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涉及村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他们在集体行动中并不在乎共同利益的实现,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和机会主义使各个主体难以积极参与治理行动。奥尔森制定出“选择性激励”来治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为行动中的个体提供动力机制。在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中“选择性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导致治理主体“搭便车”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为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克服“搭便车”行为,提高村民、企业、地方政府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行动积极性,增强各主体治理能力。
4.1 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
村民是农村水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农村水环境的优化离不开每个村民的行动。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既要鼓励村民的环保行为,又要加强对村民的不作为及环境破坏行为的处罚。
4.1.1 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 奥尔森认为法律是解决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最强有力的手段,但中国法律对于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规范尚不完善。2018年《环境保护法》将农业环境的保护纳入法律范围,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但并未对公众不积极履行环保义务的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确规定。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补偿权,使村民在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不履行环保义务的行为进行处罚,以罚款、拘留等法律惩处来震慑村民,激励村民自觉履行保护农村水环境的义务,避免其采取“搭便车”行为。
4.1.2 落实保护性耕种补贴政策 发挥保护性耕作補贴在农村水环境治理和保护中的作用,完善与农村水环境相关的补偿指标,对使用生态友好、保护水资源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行为进行经济上的补贴,以个人利益的满足推动个体参与集体目标实现的行为。
4.1.3 建立农村生态文明奖惩机制 发挥声望、名誉等因素对村民的激励作用,对保护农村水环境、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村民给予表彰,对破坏农村水环境的行为通过公示、教育等形式给予处罚。利用奖惩机制,鼓励村民检举揭发其他村民和企业破坏农村水环境的行为,监督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与破坏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抗争。
4.1.4 建立农村水环境自治组织 农村水环境自治组织打破了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村民集体作为“大集团”行动的规模,实现了农村集体行动的“小规模化”,提高了治理行为的有效性。村民以农村水环境自治组织为载体,实现共同利益的紧密联结,通过组织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进行环境抗争行为,提高公众参与影响力,以组织活动成果刺激村民参与水环境治理。
4.2 完善企业激励机制
企业作为“经济人”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既要依靠法律、政策手段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又要发挥经济激励手段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刺激和引导。
4.2.1 完善企业水环境治理法律体系 当前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企业的违法成本远远高于遵守法律的成本。《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对不按固定排污、污水处理不达标的行为处罚标准,但处罚力度远远不够,水污染处罚相关体系和标准还不够完善。应建立全方位的水环境污染相关环保法律体系,包括企业水环境排放评价及标准、水环境监督及执法体系,提高企业水污染惩处力度,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
4.2.2 建立企业水排污权交易制度 将排污权引入农村水环境的治理之中[8],政府在农村流域一定范围内确定排污的最大范围,企业通过水排污权交易制度,实现排污额度的转移。出售水排污权企业的水污染治理成本通过排污权交易得到经济补偿,降低企业污水治理成本,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不断完善排污技术,提高治水排污设备的使用率。购入水排污权的企业付出了排污成本,激励企业对生产中的排污行为进行控制。排污所得的费用作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给水环境治理,最终实现流域内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9-11]。
4.2.3 建立企业水环境信用体系 通过水环境信用体系将企业水环境保护的行为与企业信用联系起来,以具有强制力的约束手段引导企业主体的水环境信用行为。信用体系影响企业信贷、补助领取、评先评优,利用经济利益与企业社会形象双重因素激励企业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 4.2.4 完善税收优惠补贴政策 在水环境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对治污企业、环保创新性企业、生态友好型企业等积极承担农村水污染治理职责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在合理范围内通过降低税率、返还税收、延长税收期限等作为奖励。
4.3 完善政府激励机制
地方政府是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只有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克服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才能发挥政府在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导作用[12]。
4.3.1 转变官员考核模式 在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中,破除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指标的考核标准,将政府水环境治理成果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水环境治理考核指标的激励之下,将水环境利益转变为部门利益、官员的个人利益,以促使政府官员转变思想观念,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生態保护,推进农村经济与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3.2 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机制 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机制,对为发展经济而不顾农村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地方政府进行问责,避免出现损害农村水环境的盲目决策。约束在集体行动中态度消极的行为,严格处罚各个区域、各个层级的“搭便车”部门和官员。
4.3.3 建立水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面对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环保、水利、农业、林业等部门之间相互观望的“搭便车”行为,建立农村水环境治理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职权范围,协调各部门的行动,使政府能够统一行使水环境治理的公共职能。
4.3.4 完善政府环保机构体系 面对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乡镇、村级环保机构缺失的现状,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环保机构体系,加强政府自上而下的环境监管能力。在乡镇一级设立环保机构,委派专门人员,分区域对该乡镇各个村的水环境问题进行管理,动员村民参与农村水环境的治理,建立完善的农村水环境治理体系。
5 结语
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村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忽视公共利益而采取“搭便车”行为。本研究构建完善的农村水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企业激励机制、政府激励机制,克服治理主体的“搭便车”行为,激发村民、企业、地方政府在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活力,实现水环境治理的多元参与,打造美好的农村水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R]. 北京:国家生态环境部,2019.
[2] 莫欣岳,李 欢,杨 宏.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水污染现状、成因与对策[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16, 38(5):1125-1129.
[3] (美)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4] 黄森慰,唐 丹,郑逸芳.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7(3):55-60.
[5] 杜焱强,苏时鹏,孙小霞.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3):321-326.
[6] 张 君.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J]. 理论导刊,2014(2):20-22,26.
[7] 曹新富,李美存. 我国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困境及出路[J]. 江西农业学报,2017,29(2):133-136.
[8] 郑开元,李雪松.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2012(3):162-165.
[9] 张劲松,任远增.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J]. 晋阳学刊,2013(2):108-113.
[10] 张露露,任中平.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4):1-5.
[11] 吴小建,徐和平. 多元共治:水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之道[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3):13-17.
[12] 罗文君. 论政府在环境保护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的启示[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8(1):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