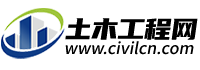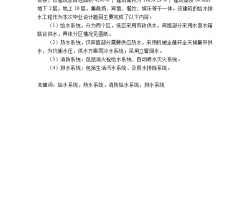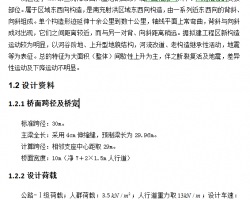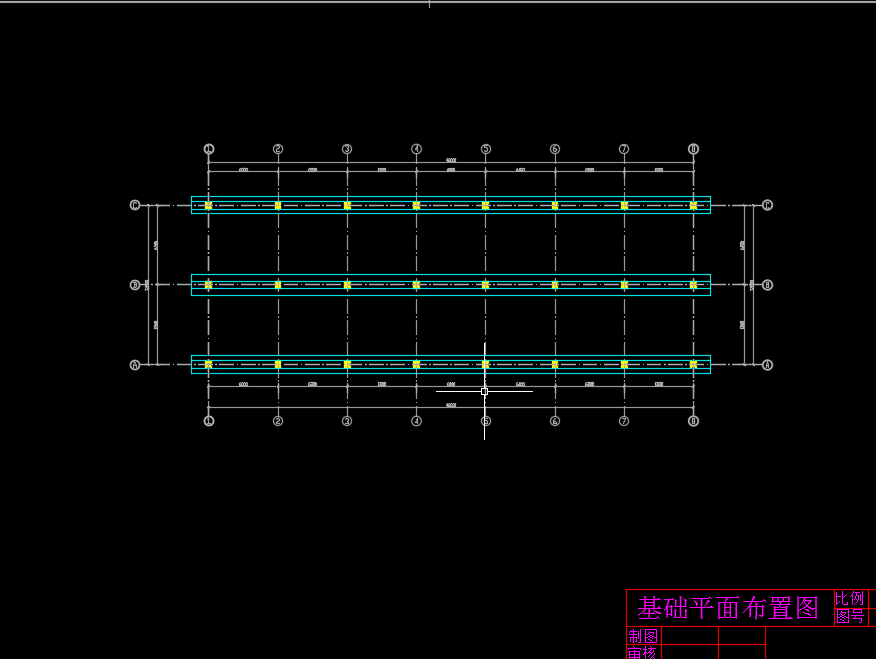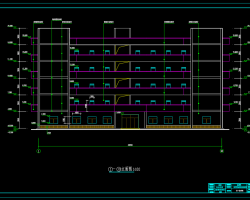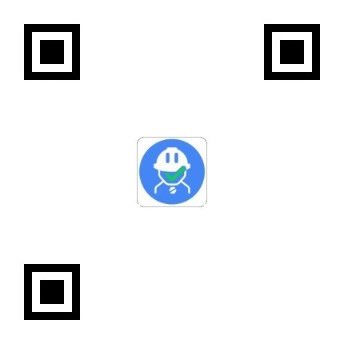1、有针对性的收缩研究范围,只就城市本身谈论城市,进而界定出城市建筑的定义,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除了对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参考。因为城市在存在上是语言性的,我称之为城市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也是论文上篇的主题。如果说过去我们把语言当做工具或者装饰,现在我们把语言视为符号或真实。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平行的评介哲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城市建筑学,因为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都在20世纪被以某种方式重新评价,这也是城市建筑学语言学转向所发生的精神氛围。
2、在城市建筑学的范围内引入语言学观念,并非为了减少建筑语言的模糊性,只是为了理解它,或者,帮助它建立这种模糊性,并试图寻找一种结构,使这种模糊性有章可循,用符号学的思考使之形式化,这就是论文下篇“迷宫”一章的主感。所谓迷宫,就是城市在结构上的一种多元语言的聚合体,里面包含着现有专业建筑辞典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是每一座城市都曾达到或将要达到或正在背弃的存在性格局。
3、当把城市看作一种类似于语言的现象,就意味着我们抛弃了城市历史的“发展”观念,而是谈变化变异的修辞理论,谈论“现实品”与营造性的转换。真正的结构理论是不谈“创造者。个人的,由此,我们可能重估古典申国的城市建筑学,多元的阅读使那些陈旧而古老的城市开放,其本身的意义也由于新的阅读而改变。它不再是一个己经无用,已在死去的历史事实,而是一个仍在运动着的人类学的事实了,因为任何所谓历史的观念都不可能把它完全表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离开了线性发展的时间,而以一种拓朴学意义上的,在模度上自由伸缩,在时间上自由滑动的”一般构造单位“,回到人类学意义上的城市本身。它所参照的,主要是列维斯特劳斯经过结构语言学改造过的人类学。做为下篇第二章的主题,要想对城市的存在性语言做一全面的估计,那种以”某某主义“命名的理论语言就会无的放矢。这里有一种历史感一一非历史的历史感。
4、如果说对一座城市,改变语言,改变分类,就是一场城市的语言革命,那么真正的语言批判不是去“判断”,而是无前提的投入城市,以在场的姿态去区分,辩异和一分为二。这种结构性的寻找本身也是设计过程,因为本文,无可归类的文体设计,从阅读开始,设计也就开始。这里描述了一种对城市的,内部经验“,如果这种设计有一种实在性,真正回到了城市实物性的事物本身,它就在于,没有预定方法,不是依靠方法上的统一,而是无前提的一个纯粹设计过程。理论家,建筑师,城市居民处于同样的困难环境中,他们回到存在的唯一障碍、最后的对象就是:言说城市的语言。要想松动它,摇撼它,下篇第三章的戏剧化话语模式可能是一个选择:空的剧场,事件爆发之地,难以名状的城市”内部经验“,即如罗兰巴尔特所说,”对任何语言,天论是虚构的、诗意的或话语的而言,都是共通的,因为从此以后它就是语言本身的真实。“(《批评与真实》礼)
5、无可归类,打乱分类的本文抹去了理论家与建筑师、规划师直至工匠的表面区别,只剩下城市的营造本身,从此以后,一个虚构城市的想象者、营造者只以他对城市建筑语言本身的自觉性为特征。他体会着城市建筑语言的深茂多义性的矛盾而不是它的工具性和美感。这种性质,在本义而言的语言干,己经存在。它的模式化建立即从一最小E别单位开始,不是去发展、连接,云制定框架式的结构和统一的宏大场面,而是以转化、变异的原则,不连续、不确定、无定向的做推论,零敲碎打,这种城市设计模式显然是属于语言学类型的,但它也是对分离性、层阶性、稳定性的专业建筑语言的最后违抗,也是论文下篇第四章的主题。
这种研究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求文并不想去决定什么,建筑师只是提供一假定的虚形式,但并未决定它,它的不确定性是纯粹的。这种非判断性的价值是传统理论观念所最难以理解的。但我坚持认为,只有用语言去谈论城市建筑的语言,才可能达到与城市本身最大程度相符的真实。激活存在,唤醒存在,走向存在,为了存在,批判的对象就是语言本身,就是城市建筑学本身,因此,它的价值就是那种不断定的形式价值,就是留给自发性,无权势的,往往是小的营造单位与活动的条件,它就是这种语言的秩序性、系列性、破坏性、解放性与游戏性,就是有限决定下的自由放任。这里关注的不是造型,不是功能确认,而是观照着城市建筑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在语义上的含混与开放。它们以一种并不夸张的方式,消解流行的巨型结构,这种力量和造型毫不相干,和尺度毫不相干。当然,我几乎是本能的偏爱小尺度,小建筑的密集群簇,它们是城市中弱小的,无权势的、偏离正轨的、被遗弃的东西。从这些东西对生活的恰切性出发,我产生了一种观照城市及其构成的新方式。我毫不迟疑的站在无权势的、本文性的设计话语一边,想象着、实验着一种有节制的、不过分的、无权势的小单位的差异共同体;这是一种理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需要所有的理想主义,这他有点消极,“顺其自然”这句中国话,本身就是消解性的,让惰性的事物自我消解、自求解放的意思。在这个各种积极的力量将城市申平常生活全面制度化、专业化、严肃化、全面毁容的时代,有必要、有耐心去坚持一种消解立场,并希望藉着这主场,探讨么是属于申国城市自已的设计语言,在城市中增加存在,捍卫自由,这才是“虚构城市”的价值本义。
用“虚构城市”做为一篇城市设计论文的题目,一个自动发生的效果就是,它使“城市”这个称谓变成一个问题·有人会问,既然要虚构“城市”,那么如果暂且把“虚构”这个略显吊诡的词存而不论,“什么是城市”就是一个绕不过去,必需回答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那本名为《看不见的城市》①的小书:在书里,他谈到按照天空星座建造的城市,建在水底的城市,一半在建造一半在拆除的城市,吊在峡谷间绳索上的城市,悬挂在林立的管道上的吊笼群簇的城市,在活的城市的夜晚必定出现的死去的城市,一个以他丰富的吓人的阅历也不曾见过的一座名叫杭州的美丽城市…,但是最终,他也没有一个关于城市的抽象定义,也许,“城市”就象海德格尔②眼中的“存在”一样,根本是一个不能问的间题。不过,在书的结尾,做为这本对话体小书两个对话者(马可波罗与忽必烈)之一的忽必烈发现了一个秘密,马可波罗自始至终也不提起一座城市的名字,那就是威尼斯,他的故乡,他用来探索世界的起点,也是他最后要归去的地方。于是,马可波罗嘴里所谈的那些城市,至少有一百个,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就都是威尼斯这座根源性城市的变体与想象中的推论,而对马可波罗来说,这座城市是不能说的,似乎一旦用语言陈述,它就将在记忆中消失。
不能说不等于不能体验。相信很多建筑师都有体会,一座蕴涵丰富的城市会因一套习常的专业描述变得干枯,也会因一个个所谓的设计变得失去活性,这是当今城市司空见惯的现象。马可波罗不能去说威尼斯,除非他在那里,在场,在场就是在那里而不陈述,他也可以离去,那座城市仍然鲜活的存留在他的“记忆”中,但任何直接的述说都会一点点的消除这座城市的生气,也就是它同时并存的复杂性,那种诸多差异性事物欢乐的同居现象。城市一词所指的存在,于是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或如维特根斯坦③所说:“神秘的不是事物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他又说,“对神秘的事物,应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如果言说城市是体验城市的敌人,文字的论文似乎就不是恰当谈论城市的方式,也许可以换种方法,比如在一座城市申四处游荡,画下几百张草图订成一册,不分次序,也没有页码;或者把论文在某城市中一天的活动,没有什么目的,想入非非的几句插话,拍成一部记录短片,诸如此类;也许最有启发性的论文就是文字、草图与影像等不同文本的混编,用不同文本互文性的影响消解或丰富文字语言。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马可波罗不仅在说,而且说的有趣味,让你感受到对城市存在在感性上的增长。或者说,躲在书中的卡尔维诺我到了一种恰当的处理语言的写作方式,一种使诸城市世界在存在性质上不缩减的方式,从最直接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方式的运用:1、不用概念;2、不用欧式几何语言;3、不把城市傲历史次序,文化等级,大小规模,功能类型的划分。
1.某种意义上,《看不见的城市》中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位“虚构城市”中的建筑师。在忽必烈的关于“什么是城市”这个基本问题的追问下,他并没有退到一个关于世界城市(他的游历是世界性的)的统一的抽象概念,而是逼到了一个具体的城市一一威尼斯。他在旅途中的每一座城市中都看到一个威尼斯,在每一次的看中都叠加上一个对威尼斯的回忆,但没有一次是概念性的判断,因为他在每一次的看申都能看出纯粹物质性的差异来,石头,泥土、木材的肌理,身体的姿态,心中的虚像,营造方式的区别,生活方式的差异。他不是用威尼斯去对这些城市做解释,也不是用这些城市去解释威尼斯,而是在思考中成长起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份理解,换句话说,他越过一座座城市,也就越过了关于这个世界上人如何在城市申生存的一个个命题。最终,他在头脑中建立起了关于这个世界上诸多城市可以差异性共存的异质异构体,包含着和生存有关的最基本的问翅。于是,威尼斯,这座具体的城市带上了几许抽象色彩,它不再是有关经验理解中的城市,而是一个可以同时承载一切生存意义的城市,包含着一种既非经验概括,也非抽象定义的活的形式,可以恰当的称之为城市的“虚形式”(见罗兰巴尔特④《批评与真实》P59,“正是这些重要的虚形式,使说话和操作成为可能”。),内聚着关于一切城市的“虚义”。“虚构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城市“虚形式”的探索,因为这是一位建筑师可以如实看待城市本身的前提。不能看到城市本身,一切关于“什么是城市”的答案都是不解其意的。如此,我们可以体会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他可以说是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了)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
2.在马可波罗这位想象中的“虚构城市”的建筑师的话语中,最打动我心的就是一种浸透在生活中的轻松感,这和忽必烈,一位固执于概念的建筑师原型那无法摆脱的焦虑恰成对照。某种意义上,相对于建筑学科的成见,马可波罗的话语是犯上违禁的。建筑学科从来没有明言,却波所有建筑师遵守的终极教条就是:你不能用城市去谈论城市,就象你不能用语言去谈论语言。因为一旦越过了专业语言的基苯命题,我指的是笼罩在我们建筑学科上的典型欧式几何语言的西方话语范式,一旦放纵,就有某种不可靠的东西“蔓延”的危险。那就将使专业权力的权力,语言的语言成了问题。你如何可以用一座具体的城市当做某种关于一切城市的普遍的形式原则·这就是卡尔维诺的马可波罗所做的,他用这种方式成功的绕过了做为建筑学科基础的理论元语言,使得某种尚待澄清的抽象概念带有感官具体性,那种来自现场性体验的轻松是使一切关于城市的理论解释和设计原则统统失效的轻松感。在对一个又一个城市的纯粹描述中,没有欧式几何语言在上的视角,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总体“布局”的图景;也没有任何在下的视角,即透视的视域;没有在外的眼光,如城市的轮廓或街道,广场的立面;也没有任何在内的观察,即所谓内部空间的感受。有的只是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若千零碎的细节,乱糟糟的,却能凸显一座城市的特质和观察者的敏锐,让人佩服,这里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恰切,把我们无论关于在现实中的实有还是想象中的虚有的城市的模糊的影像和同样模糊的情感还原为清晰的图景,也透露出一种观念,一座城市就象一个人,不能用几何语言去切割,不能切割出在上的精神和在下的肉体,也不能切割出在上的重要建筑事物和在下的无名房屋,迟早要切去的畸胎。
马可波罗的城市观念不是欧氏几何学的,他的体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体验只能放在拓扑学的观念中讨论。他的拓扑学观念是拉康⑸式的,谈的不是内与外的问题,也不是上与下的问题,而是关于城市中的事物与事件运动的正与反的问题,在一个非欧氏几何形状的清楚边界内,城市事物围绕着某个尚不存在的场景,不停转动、开岔、分裂、拉长、重叠和拆叠,显露出某种重复的外表,但决不掩饰差异的存在。同样的体验,我们也可以在象苏州、北京旧城,直至皖南的诸多村落中得到,它们共同构成某种拓扑学意义上的差异共同体。皖南一个几百人的村落和几十万人口的苏州在结构上是等价的,拓扑城市与城市的大小无关,是关于城市的城市,我称之为拓扑城市的第一原则。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对每一座城市的描述都极富物质性的质感,以及人与建筑重叠在一起的形象性,但却没有任何可以归结为平面或立面或立体的造型原则,这本书当然不是传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调查笔记,也不是们建筑师纯主观的臆测。它对城市中物质细节,人体姿态,甚至一个眼神的观察使人察觉到身边大量被忽略的日常事物,而它对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城市描绘又让你感到一种无时间性的预言性,没有一座是百分之一百实存的,但也没有一座是不真实的,甚至比经验中的城市更真实。
观察不是记录,而是批评。马可波罗不是运用语言说城市,而是对语言言说城市的潜能做讨论论,更准确的说,是对一座城市如何自我言说做讨论。于是关于威尼斯这座城市的讨论就分裂为一种一分为二的言语。实际上,是否是威尼斯无关紧要,它可以是一位言说者刻骨明心的任何一座城市。问题是,在关于城市的习常经验上加上结构性体验,在城市设计的第一次设计上加上第二次设计的重叠之物,于是,语言反思着语言,打开一条无穷尽的路,威尼斯和一百座城市的关系就是威尼斯在西排互映的镜子之间的变形影像,这就是关于城市的拓朴模型,它并不需要提炼成什么纯粹的抽象规范,这就是语言性批评的含义:“并不是去判定,而是去辩异,区分和一分为二。”《批评与真实》,P6)这同时也是“虚构”,因为这个模型中没有功能,但有功能状况,所以说它的形式结构是“虚的”,“虚空就是最大的充实”(见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马克波罗在威尼斯与一百座城市之间的相互言说中,没有丢失威尼斯本身的一样东西,却使这座城市本身在想象的推论申不断成长。
3.如果说《看不见的城市》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出色的“虚构城市”的写作,它在历史次序上的混乱是别具理论价值的。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有忽必烈时代的杭州,大运河边的红墙绿瓦,低垂的杨柳,也有飞机场,洛彬矾,好莱坞和纽约的第五大道。问题是,它们都是对威尼斯这座城市同时性的不断重造。于是,历史性前后取替的线性时间观瓦解了,这里至少包含了三个观点:
1)特别和列维斯特劳斯⑹的人类学思想有关的“结构时间制”:城市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遗存都是等价的,是各自特定范围内的独立成就,携带着对生活特有的欲望与针对性,并无因历史次序造成的优劣之分;
2)把城市申现有的一切都做为某种杜尚⑺意义上的“现成品”加以接受,这里对城市的爱欲不是来自摧毁,而是来自它现存的裂缝,缺失和离题的处所,于是,设计原则变成了在“现成品”之间,之内的转化原则;
3)城市的拓朴模型是一个无时间,无定向的多义模型,它既预言又回溯。
《看不见的城市》就是虚构城市,它在文化上显然不是断定性的。通常的“文化”定义来自“事实”等。而建筑学不加思考就加以认定的“事实”通常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的禁忌,主流文化和卑微的市民文化的分歧(违章,随意搭建,自发营造与城市规划的法规冲突),“分歧变成分裂,分裂变成错误,错误变成罪恶,罪恶变成疾病,病症变成怪物”(批评与真实,P8)。在我看来,中国城市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那些被写上“拆字”的建筑通常比那类高尚的文化建筑更有价值。它们无权无势,但紧贴生活。城市规划的法则是排他性的,一种意义的确定就意味着其它意义的排除,与之相反,《看不见的城市》中的思考是想象的,想象不等于胡编乱造,虚构城市的拓朴模型就是靠想象的逻辑支撑起来,它不在原始与现代、先进与落后、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为划界,否则就不能理解一座挂在绳索上的藤屋城市如何会是威尼斯这座古典名城的变形。虚构城市的模型是开放的,它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可能性。可能性不是某个人的主观幻想,它就在一座具体的城市中。
我们说一座城市的结构性存在是语言性的,也就是在说它存在的基础即是不同成分间的差别,是诸异质成分的共居。这当然不是那类总体规划或总体设计的想法,拓朴的城市模型源自“内部体验”,在这里,对结构的寻找不是小事,寻找结构就是组织世界,就是理解生活。这种理解是多义性的,开始于对最小区别单位的剥离,我称之为“一般构造单位”,能够同时承载最大可能性的情节事件,它是衡量一座城市品质的最小元素,也是建构一座城市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可以恰当的称之为“城市建筑”的东西。这里没有高低贵贱,有的只是一种针对生活的恰切性,语义上的开放,它是和尺度规模无关的。由此出发,可以认为一座皖南的村镇是‘城市的“,而象苏州干将路的开发就走向城市的反面,只是单一意义的结果,是城市存在的缩减;同样,上海的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尽管里面有着大量自发搭建,街边篷户,却是城市的,而象博物馆那样的东西则是反城市的,是压制性的语言象征。事实上,这只是中国城市在存在意义的衰退征兆。采集者退散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马可波罗回忆的成百个城市画在一张透明图片上,和一张威尼斯的全景图重叠在一起,在一座城市本身的变体意义上,各种看似不可能放在一起的功能就都如生活申的巧遇般重叠在一起了。我们从事实出发也许不能理解,但在那座城市的现场却可能体会到它精确的真实。如果说‘虚构’就是城市能承载一切意义的“虚形式”,那么,它会是一个无穷类推,以相加为原则的类型排列吗·这样的城市并不存在。与之相反,虚构运用的不是相加的原则,而是重复、折叠、重叠、错位来实行的统合原则,它的结果只是有限、而且相对简单的几个类型的组合系列,并且坚持认为,它必然和生活申的城市在最大的可能性上相符。
虚构城市就是在功能上,语义上都不可分类的城市。虚构针对的不是城市的“现实,而是更广更深的存在,存在就是可能性的同义词。所以,提出虚构城市的城市设计理念,提出虚构就是探寻能够承载城市中生活状况最大可能性的”虚形式“,就是针对目前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在存在上的缩减的。
谈论一种不可归类的城市建构,这种讨论必然是语言学性质的。人的标志就在于其是语言性动物,而语言,就是人们组织世界,理解世界,生活于世界的最基本的分类现象。分类也是一门科学,包括建筑科学可以成立的基础。研究城市,如果坚持一种彻底性,就只能从语言性的分类入手。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虚构城市的观念对我们熟悉的建筑学关于城市的知识是破坏性的,是从理论到设计的一种批评,因为它着眼的不是语言的运用,而是对语言,城市建筑语言本身的讨论。证如罗兰巴尔特所说,“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会么比语言分类更重要的了。改变分类,变化语言,就是一场革命。”a批评与真实》,p43)
在这里,不是用语言学去解释城市建筑学,也不是用城市建筑学去印证语言学,而是从分类的角度看,城市建筑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类似物。对城市最彻底的讨论只能在语言学的范围内去讨论。如果我们还记得索绪尔⑻的那个著名论断:“语言是一个纯粹的形式系统(在索绪尔之后,‘系统’一词因社会学考虑而被”结构“一词所取代)”,那么,尝试建立城市的结构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也指出了“什么是城市”这一答案应在什么方向寻找。什么样的建筑事物是城市性的·如果说城市就是一个拓朴学范围内发生的建筑性的意义共存现象,这只能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普遍符号理论之内提出。
于是,虚构城市的理念把城市建筑分解为“记号”,某种介于理性和自然之间的东西,这直接导致它不同以往的理论视角,对此拉康的说法也许是最精当的:“实例与意念不分的……观念,甚至认为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真实。用全面扩展的意象替代传统的抽象观念。”(在高等实用学校他的讨论班上)这就是我为么推崇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在对上百种城市的言说中,那座根源之城威尼斯,本身就是在互相映射中丧失了根源的,它不是一个用以解释一切的抽象观念,但也不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实例与想像的推论意念不分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触及”事实“,却直达城市中纯粹的实物。它在想象中的生长,直接于城市中那尚未被决定,被命名,在一个外乡旅人眼中显露着初次看见的新鲜性的实物本身的类的揉合。这些实物以及其本身的类的揉合,把”能指“以及”能指的织体一一本文“这几个特别和”虚构城市“有关的概念用活,从此以后,城市才被看成本文牵带出虚构城市第二个重要原则,等价性原则。虚构城市就是城市本文的制作,就是用语言谈论语言的设计与写作;它将抹消理论与设计的区别,观念与实物的区别。从此以后,理论也将成为一种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实物的能指性,也就是一种实物与纯粹的符码的距离所造成的诧异,一种可能性的意指事物将会随时爆发(或者不爆发)的场所条件,可能成就出色的城市本文。因为在习常的理论言语中,实物被公认为平淡无奇,除非我们给它一个解释,使”抽象和具体揉合“,使它们被”创造过“,反之,站在本文的立场上,在城市中,最无创造性的,易被我们习惯的理论眼光忽略的纯粹的建筑实物,可能是最”城市的“建筑元素,最具”创造性“。
做为虚构城市的产物…本文,它那不可归类的特征也制造着阅读的障碍。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有那么多新词,新概念,难道就不能说的清晰明了。”似乎这只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我乐意给一个反问:“如何能用一种词义贬损的,单一价值的言语去表达多义性的语言本身呢·”这不是一个表达问题,而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分歧。虚构城市永远指向城市的建筑语言本身,它的多义性的潜能。在一座城市中,一位虚构城市的建筑师即如一个二岁幼童,他尝试用语言本身去组织这个世界。二岁是人的语言能力的最高峰,他说不出一个人人均可认同的完整句子,只有只言片语,误用着语言,但语言的结构性质最突出,让人联想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他的语言直指纯粹的实物,但那有缺陷的,未完成的表达是抽象的,但并非抽象观念,不如说,他说着一种记号性的语言。在那以后,当他开始能说一种大众认可的言语,语言本身的这种能力就埋伏在平庸的言辞之后,当他进入一所建筑学院,就开始学习一种理论行话,当他开始学习城市设计,就用关于城市已有的知识来决定城市形象,学习一种通用的心理学以让大众心安。这种专业语言实际上是重言反复,如罗兰巴尔特所说,“(那些)词义因年代久远而可能损耗。词失去了所指的价值,只剩下商品价值,它只有交际作用,犹如一般商品的交易,而没有提示的作用。这里语言只有一种肯定性,就是具庸俗性,人们经常以它为选择对象。”(《批评与真实》,P12)
这种行话让建筑师远离城市中的实物,远离城市本身。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文学研究做为城市研究的参照,不仅是因为对语言本身的思考是二十世纪的文学特征,更是因为,如果人们总是用一种语言性的东西和世界订定关系,那么像《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本文制做,就还没有达到麻木的地步,它无休止的去提示当下城市中那难以忍受的平庸处境。
如果说,本文的制做就是在习惯的专业设计之上再加上一次第二语言的设计,关于语言本身的设计,打乱分类,解放意义,编织记号的,纯粹能指性的织体,那么,旧的引语就与我们所用的语言无关,我们知道它不能用另一种方式设计,除非能用另一种万式思考,因为设计就是组织世界,就是思考。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要建立一种新的方法,更抽象,更高效,而是掉头反向,回到城市的事物本身,并坚持城市不能简化。
虚构城市,就是用一种结构性的语言去谈论城市语言本身。甚至越过语言,回到实物,就是对以往那种不思考的城市设计的不思考。因为这种理念意识到,域市设计并不是靠着一种工具性语言去与一切可能的使用者订定一种容易的关系,而是与我们用以组织城市的建筑语言本身订定一种艰难的关系。它希望开启一条深思城市存在性质的道路,由于没有人最终能走出语言之外,深思存在,也就是城市建筑语言本身的意义机制。它将试图建立一个城市设计作品所能产生的条件或它不产生的条件,如果不能勾勒出一间独立的学说轮廓,至少应提出一种城市设计的技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