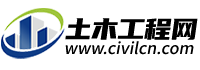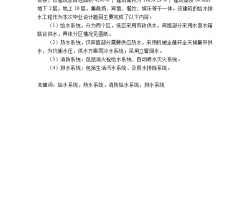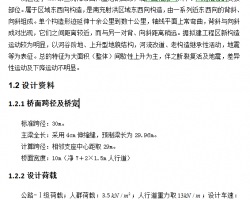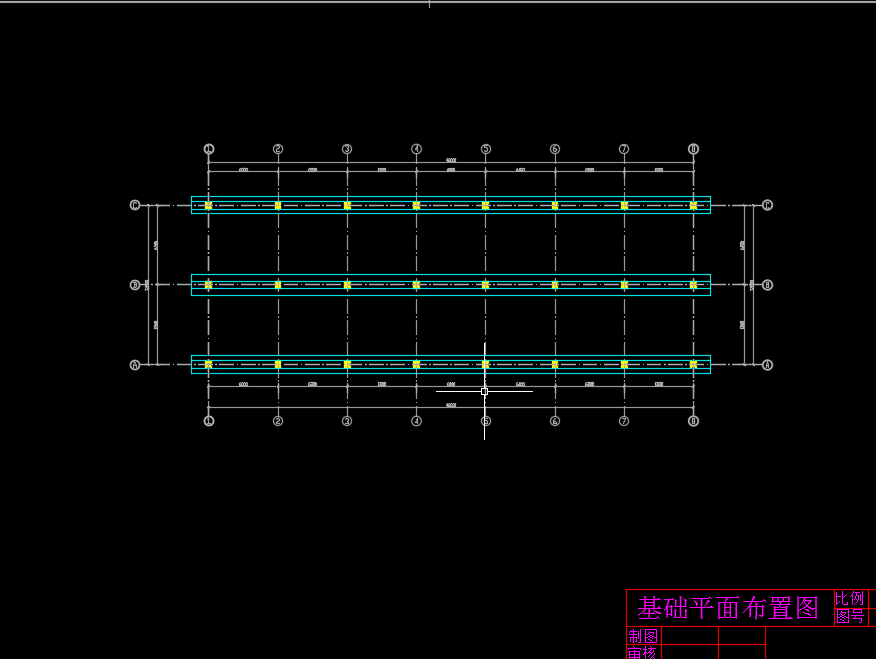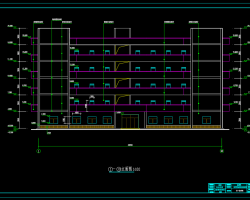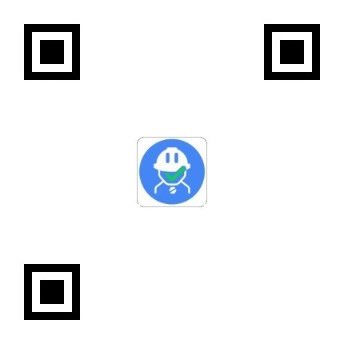人们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33年《雅典宪章》把城市分为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功能活动区,要求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以便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在最经济的时间内得以完成。《雅典宪章》还明确指出城市规划首要任务是研究城市职能,合理安排功能分区。
半个世纪后,1977年城市规划师们又在利马(Lima)制定了《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并非上述四项社会基本功能的孤立简单的拼凑,指出人的相互作用和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城市是满足人类活动要求的连续空间。这就是说,城市作为一个功能体,可以是工业城、首府、港口城市、科学城、商业城或金融、贸易、信息中心,但城市的物质形态却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群体相互作用、进行文化①活动的历史积淀。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空间也将继续被要求能进一步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今天,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已被日益关心和重视,在规划中考虑人的活动也已成为重要方面。那么人是怎样活动,怎样进行相互作用和交往的呢?这种活动又是怎样成为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呢?
概括地说,人类是一种群居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物,他们有智慧和能力,能够能动地认识自然,给以理性的抽象和概括,并把这种经心智加工而成的抽象图式、模样、道理、规范、礼节等,一方面指导自己的行为,呈现出特定的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进行物化,为具体存在物,并由特定的符号系统在人际和代际传播,这就是人把自然改造成“文化”的活动。整个人类的文明体系就是建立在众多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文化活动基础上的。在文化活动中,分享共同价值观、信仰、宇宙观和象征系统的社会群体,依照各自规律系统、习惯和常规,采取不同的行为、态度,并指导食物、住宅形式和聚落空间形态。
过去常常认为经济、技术、地理条件是建筑和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美国人类学家阿莫斯·鲁波帕德(Amos Rupoport)在1969年出版的《住宅形式和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一书中,详细阐明了住宅形式与文化间的亲密关系,认为文化因素是决定住宅形式的关键。他指出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气候和地域条件下,希腊既有封闭式院落住宅,也有开敞式独立住宅;某些生活在地球极区的民族,并没有因为当地气候十分寒冷而建房抗寒;相反在炎热、潮湿的马来西亚,华裔却喜欢居住在中国传统的封闭式院落住宅里;欧洲人竟漠视气候影响,在一些居住在封闭式住宅更为适宜的地区,坚持居住在欧式住宅里,把生活方式以及地位、权力的象征性放到了首位。因此,与其说气候、地形等对住宅有影响,还不如说文化与住宅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应该看到,文化因素对建筑形式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具有超越经济、技术的力量。也就是说建筑和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技术的制约,也受到更为强大的社会聚合力——文化的制约。在中国汉族的传统民居中,北方有四合院,南方有“一棵印”,中部有皖南民居,西部有黄土窑洞,等等。虽然中国土地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这些住宅所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但住宅型制却都是带有规则院落的封闭式平面,在空间布局和细部装饰纹样方面亦都带有共同之处,反映了汉族人民的共同伦理观和价值观,就连上海30年代建成的近代住宅——石库门,也是江南宅院住宅的变异,仍保持传统汉文化的特征。然而生活在我国云南、四川等地的各个少数民族,虽然有相同的自然条件,又经过千百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技术材料的传播,却仍然选择了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住宅形式。纳西族信奉东巴教,哈尼族信万物有灵,傣族却信佛教。纳西族有一年二次的祭天活动,哈尼族有10月作为岁首的大庆,傣族则有别开生面的泼水节。纳西族实行“阿注”异居式的婚姻关系,7月泸果湖畔有青年男女社交的“海坡会”,傣族大家庭则数代同宿一堂,席地而卧。纳西族在住宅内设火塘,放灶神,哈尼族把龙树当作一寨一户的保护神,傣族则崇尚佛与火,村村有佛寺,家家有塘火,塘火常年不灭,不准跨越。在他们的心目中火具有神圣性和象征性。这些不同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住宅形式和聚落空间的变化和差异。傣族的竹楼,白族的“三合一照壁”,纳西族的悬山屋顶和山墙悬鱼,哈尼族的蘑菇状土掌屋,形成了绚丽的云南民居系列。更为有趣的是这些社会群体毫不雷同的聚落空间和布局。在纳西族村寨里,每每有河,水被引入各家,村寨中住宅则围着中央“四方街”布置。“四方街”是平坦方整的广场,两侧是商店、集市,富有熙熙攘攘的生活情趣。哈尼族村落保留着古代遗风,以水井为村寨公共中心,住宅围水井,顺坡自由位置。白族生活中心则富有文化娱乐气息,庙和庙前戏楼构成中心广场的主体。而傣族则把体型高大、装饰华美的佛寺安置在村落的显要地区,作为街道对景和生活中心。人类在把所依存的外部世界“秩序化”的过程中,赋于某种意义和价值,经数代人的选择、创造、追求、积淀,丰富了建筑形式并形成了具有哲理和个性的聚落空间形态。
城镇作为文化物质形态可以分为2个层次,一是构成城市的元素,如建筑物、街道设施等;二是城市本身的结构和形态。这两个层次都从属于文化结构的器物外表层,但在深层结构上却与社会群体的心理素质、社会制度、处世方式、价值观念都无不息息相关。
这种建筑和空间在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差别和影响,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古代希腊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摇篮,而先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母。公元前5世纪,世界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出现城市型居民点的时候,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就存在着高度发展的城市,虽然当时同处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奴隶制时期,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模式却有很大差别。这个时期,希腊正处于由小亚细亚中心向雅典西移,城邦民主制逐步完善并走向全盛的时代。这30多个城邦国在亚历山大把它们统一以前,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执行着公民的民主制度,“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①因此“希腊精神有两大特征:一是构成希腊性格中的美的个性,一是那种追求真理、酷爱独立、自由的性格。”②古希腊文化具有起源于各个独立的个体的特征,30多个城邦国的城市空间构成元素虽然类同,但城市空间形态并不完全相同。
米利都城(Miletus)是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在波斯人破坏城市后不长时间里规划重建的新城。这个城的构想代表了古希腊人对其制度、生活、理想、观念的最直接和具体的表述。在这个以商业、军事为主要职能的城市里,由方格形路网组成城市骨架(主干道宽约5~10米,次干道3~5米),拥有居民1万人左右(包括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农民、手工业者和为国奋战的武士阶层),分别住在3个居住区里。居住区中央是广场和其他公共设施。由此城市空间可分成3个层次:私有空间——住宅;半公共空间——剧场、浴室、竞技场、议会厅等为自由民所享用;公共空间——祀神和商业活动的神庙、广场、商场等。城内低矮的住宅与高大的公共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剧场、竞技场、浴室等公共建筑散置在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的地区。全城以广场为核心构成城市生活中心进行各种公共活动——议政、拜神、沐浴、社交、集市买卖、杂耍。在这里有时还宣布刑法和开展辩论,它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公共空间。古代希腊人具有极高的思辨力,他们从“什么是自然本原”出发,常常进入“怎样才能达到理想人生境界”的思考。米利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对它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表达了古希腊人对理想人生的理解,人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以及他们参与公共活动比家庭生活更为重要的观念。
《周礼·考工记》相传是春秋晚年齐国官书,是与米利都城同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古代正式记录的文献。它比较全面地记叙了周人的城市规划体系。春秋时代,中国处于小国林立,互相征战的时期,这些国家政治各异。这些似乎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同时又都属于奴隶制社会。但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凌驾于这些小国之上的最高政治权威——周王、殷帝。这是与古希腊城邦国有着最重大差别之处。小国都处在大一统的“王权神授”的东方专制政治统治下,社会内阶级结构与父系氏族血亲关系相结合,掺合着“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职业种姓制度,形成垂直隶属的人际关系。同时伦理、礼法从宗教、教育、制度、观念上对这种氏族种姓阶级制度的规范进行保护,使中国人一开始就约束于家长制那种自然伦理之下。这种人与天、人与人的关系,在《匠人·营国》这一记述城邦国建制规范的文件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个文件以图式语言规定每一个城邦国的城墙每边长9里,各有三门,城内南北和东西各有三条大街,街宽均为车轨的9倍(约18米宽)。在方格路网的城市中央为王宫,宫两侧设祖庙和社稷坛,朝廷在前,集市在后。方形、轴线、对称的平面布局建立起简洁、严谨的社会秩序;王宫为主体意味着王权尊严,甚于神灵的礼制观念和对宇宙的概念;在以家庭为本、垂直隶属的社会结构里,市民们除了住宅外仅在城内共同拥有“一夫”之地的商业公共空间,完全被剥夺了古希腊人能自由表达意志的那种公共空间和场所。中国古代哲人常常热心争辩“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这个问题,《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城市模式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他们推崇整体结构的完整性和社会结构的层次性,与古希腊主张独立自主的个体完全不同。
世界上除了东、西文化外,伊斯兰文化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伊斯兰国家里,家庭生活被视为神圣。他们要求有高度的私密性,因此住宅封闭。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的内院设在住宅中央。与中国人一样是几代同住的大家庭结构,但住宅平面并无中国四合院里以方向代表长幼尊贱伦理关系的现象,却强调内外有别,常常设置视线遮挡,使家人和妇女可以自由看人而不被人看。由于教义中奴隶和苏丹在神的面前同样平等,故住宅外观区别不大。城市由住宅和住宅前弯弯曲曲的道路组成社区,各社区内住着同教、同种族或相同行业的居民。社区间是带状市场。城市中心由清真寺、庙宇、宗教法学院和综合性市场组成。居民的个人行为场所(Befavious Space)主要是住宅和社区,妇女的活动空间更小。社区是居民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亦是一种社会地位和亲密度的表示。每个人在社区里有强烈的团体义务感,通过社区整体参与城市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社会结构、生活习俗、与城市空间形态共为一体,成为城市景观特征的基本依据。
至今西方城市仍保持着古希腊文化精神,拥有众多的广场、绿地和各种开敞的公共空间,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由教堂、市政厅、市场组成的城市中心。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的广场闻名于世;法国巴黎由一系列广场、绿地、林荫道组成城市轴线;东方城市则延续着古代东方文化的精神,以庙会、商业街等带状公共空间向大众开放,如日本东京的银座,北京的王府井,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等;而伊斯兰教城市里清真寺和市场占有显要地位。
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一方面取决于组成元素,另一方面还在于设计手法和形象。后一方面同样亦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美是什么”的问题,西方美学家曾争论了两千多年,从古罗马朗吉弩斯开始就提出了崇高与优美为命题的西方美学观点,“力量、直线、粗糙、巨大、锐角、方形是崇高;曲线、圆形、小巧、光滑是优美”(朗吉弩斯著:《论崇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美是由度量和秩序组成的”。一直到现代,法国人仍认为“条理和逻辑是一种美”。西方人以探讨审美对象的外在特征为出发点,表达了追求理性,征服自然的价值观。由此产生了著名的法国几何对称式园林和意大利台阶式园林,地毯式花坛,修剪呈圆形或锥形的树木,形象逼真的雕塑,一览无余的空间,反映主宰世界的意志和追求崇高和优美的情趣。
中国从战国孟子时代形成了阳刚美和阴柔美的美学体系,认为阳刚之美,如长风出谷,如崇山峪崖,如决大川,如鼓万勇士而战之;阴柔之美,如清风,如云雾,如幽村曲涧,如人有喜、有悲。用阴阳这两个简约、含蓄的字为核心,描述了一种情和境,用情和境来说明客观事物的内在精神和以意取胜的艺术表现原则。在中国园林中,总是以山水为景,无山要堆山,无水要造溪,讲究小中见大,对景、借景,造成婀娜多姿的自然景色和曲折多变的空间,以诗一般的景,激发游人怡然自乐的情,最后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表现了深藏于中国人内心崇拜自然的意念以及追求和谐之美的哲理思想。
然而,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价值观也会改变。60年代末西方现代环境设计理论的奠基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景建筑学和城市规划教授麦克哈格(I.McHarg)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新的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为人与自然合作才能共同繁荣,主张环境设计应从强调对称、轴线,表现人的力量转向表现自然美,以便最大限度保存自然,合理使用土地。此后美国城市的广场和绿地都开始转向“自然化”的设计。
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也都在近几十年里,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纷纷在城市中建立市民广场和休息绿地。日本名古屋在长达几公里的城市中心,建立了久屋大通公园,集东方步行街和西方广场为一体,成为广大市民喜爱的场所。中国近年很多城市也正在探讨把政治集会广场改造成市民生活中心广场的途径,并在城区开辟了很多绿地和小广场,为城市空间改造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总之,在城市物质形态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群体的文化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