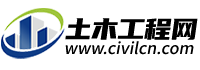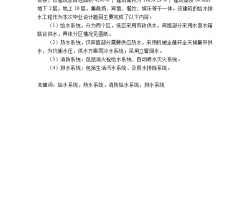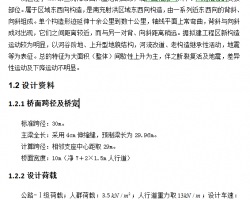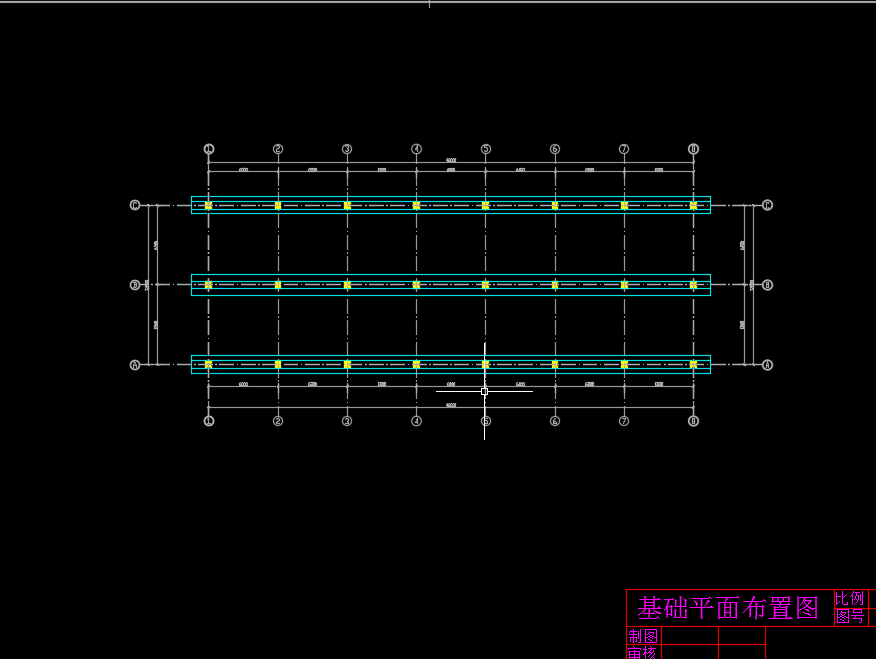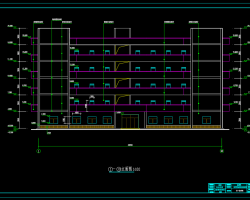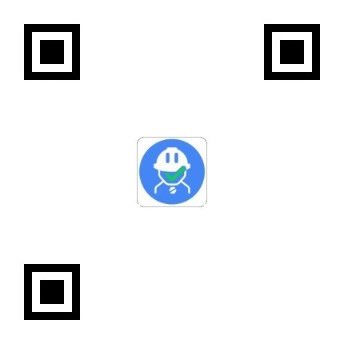代城市具有人口高度密集、流动性强、人际交往频繁等特点。一旦发生城市灾害及重大公共危害事件,不仅会危及本市市民生命财政安全,带来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往往波及农村和其他城市,甚至影响社会全局。因而,城市应急管理应当更具超前性,走在其他区域前面。
一、城市应急问题: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城市应急问题,既是一个早已引起人类关注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崭新社会内涵的新问题。说是“老问题”,就中国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唐朝已有关于火灾报告的规定,《唐律疏议》云:“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从本失火罪减)”。即凡发现起火者,均应报警并与火场附近人员共同扑救;如果发现起火而不报告不扑救,则应治罪,其刑罚比照失火罪减去二分之一。宋代还出现了“潜火队”这种相当于今天的消防警察的专门力量和“军巡辅”这类专司消防的机构。以后,在洪灾、地震等灾害应急方面,都有大量探索。说是“新问题”,意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急管理,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核电技术、生物技术出现之后的事情。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人类防范灾害的措施、手段日益进步,对火灾、洪水、地震、台风这样一些灾害,采取了许多防范和应急处理的新对策和新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事故的发生,诸如核辐射、有毒化学物质泄漏、新病(毒)种扩散、危险物种侵入等等,可能造成不仅是大面积而且是新的未曾认识的人类危害甚至生命威胁,从而成为城市应急的新领域。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在核辐射事故应急方面,由于1979年美国的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列核事故震惊了世界,各国际组织,特别是IAEA,采取了有力措施援助前苏联;各核电国家积极地吸取教训,检讨并改善自己的应急计划和应急准备;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对自己的核设施和核电站的应急计划和应急准备作了全面检查,采取很多措施加强和改进应急工作,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中国核辐射防护研究院设立了辐射事故应急技术支援中心,作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辐射事故应急技术后援组织。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在化学事故应急方面,近年来,我国也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化工部于1997年发出《关于实施化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加强重大化学危险源管理的通知》,国家化学品登记注册中心和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会员企业已于2002年7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了化学事故应急响应服务协议签字议式。在病(毒)疫应急方面,我国已于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如江西省于2003年3月着手组建反恐医学应急系统,组织开展反恐培训,加强传染病菌(毒)种管理,防止因菌(毒)种扩散或遗失,引起传染病发生和传播,防止生物恐怖活动;建立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疫情、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和反恐斗争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
尽管如此,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应急管理仍然滞后于灾害事故的应急需求。在一些城市,由于人口膨胀迅速,城市扩容较快,人们对城市管理、城市经营等各项工作还比较陌生,一些决策者,首先注意的是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以及市民生活质量,对于尚未看见的市民可能遭遇的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生命安全的应急问题,注意不够,研究不够。有的城市行政上虽然“升级”,但其应急管理系统还是老“版本”,并未“升级”。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城市的应急网络不健全,应急机制不完善,应急手段比较落后,一旦灾害事故突如其来,“应急神经”就显得反应迟顿,决策者不能快速、高效地作出以救生为核心的减灾决策。特别是对新的灾害事故由于缺乏科学预测和先期预案,往往不能使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大量灾害事实和应急实践,特别是当前许多国家正在遭遇的这场非典型性肺炎(SARS)病疫,使许多领导者特别是城市领导者寝食难安。严酷的现实表明:城市应急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不可小视的问题。应当说,它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又非常紧迫的重大问题。一个城市是否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应急功能,不仅关系到城市本身的发展或城市化进程,更关系到广大市民甚至全社会的生命安全、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还将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作为城市领导者、决策者,不能不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智慧与能力,深谋远虑,在大力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切实抓好城市应急管理工作,增强灾害事故应急处理能力,确保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宜人化”生存生活空间。
二、每个城市都应建立灵敏高效的应急系统
所谓城市应急系统,就是能适用于城市灾害事故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网络。建立这种网络是加强城市应急工作的重要内容。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组建了国家层面的专门应急机制──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它为整个美国的应急管理设定全部操作标准和指导纲要,开展各种应急培训,为各州及灾害发生地提供财政支持,协助联邦划分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职责,明确灾害事故发生时,人们应该与谁联系,怎样联系等等。韩国针对水灾、火灾频繁,还时有家畜口蹄疫发生的现实,建立了中央灾害对策部,作为常设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推进各种防灾对策,审议国家防灾基本计划,协调各地的防灾工作,制定年度防灾计划等。英国也于2001年设立了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负责协调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和志愿人员的紧急救援活动。该秘书处下设3个具体职能部门,包括评估部、行动部和政策部。分别负责全部评估可能和已经发生的灾难的进程和规模以及影响范围,发布信息;制定和审议应急计划,确保中央政府作好充分准备有效应对各类意外事件和危机;参与制定后果管理政策,起草有关法规等。日本建立了全国危机管理中心,指挥应对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危机。国外的经验对国家应急体系和城市区域的应急体系建设无不具有借鉴意义。应当说,外国的这些应急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应急管理部门,它把所有级别和所有类型的应急工作总揽起来,统筹研究和分析,然后作出各种预案。在中国,目前虽然已出现多种专业性应急组织,包括消防、防汛、防震与抗震、疾病防控以及前面所提到的核事故应急技术支援组织等等。但是,它们都不属于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仅从一个方面履行应急职责,无法突破部门限制,而且这些机构大都担负着应急处理以外的其他职责,所以,每当灾害事故发生,它们的协调组织能力和应急处理权力都显得非常有限。平时,它们很难拿出跨越自身业务范围的灾害应急处理预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虽然建立了多种从某一方面履行应急职能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之间往往缺乏纵向和横向的贯通,即不能在运作层面上形成联系密切的网状系统。如果说,此种状况,对于像洪灾、火灾、地震以及空难、火车巅覆等不易扩散或蔓延的灾害来说,还能勉强应付的话,那么,对于像非典之类传染性很强的病疫和有毒物质遗失、危险物种侵入等灾害,就难以适应了。从非典出现到蔓延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城市发现首例患者,其他城市不能作出迅速反应的现象。这是传染病应急系统横向贯通不够、灵敏度不高的表现。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各级政府都成立防治非典领导小组或指挥中心,并由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小组”或“中心”负责人。这既说明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与负责,也说明现有的专业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缺乏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的权威,成立这种“小组”可以对已有应急处理系统的缺陷起到弥补作用,也能更好地发挥已有应急处理系统的作用。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临时应急指挥系统+专业应急处理系统”的专门网络。这种网络的效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是在灾害发生时临时组建,所以,许多应在灾害发生前做好的日常准备工作,诸如应急资金筹措、应急人力资源管理、应急人才培养、应急演练、应急知识普及、灾害保险以及跨部门行业的应急预案的制定,都难以保证。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灵敏、高效的应急系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和现场处理的权威和能力;网络是环环相扣、纵横贯通的;不是临时搭建而是常设性的。按照这些要求建设应急网络,可以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综合性应急管理系统+各专业应急处理系统”,即:由政府设立一个综合性应急职能机构,像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和韩国的中央灾害对策部那样的常设性机构,直接领导和协调各部门的应急工作;各专业应急系统负责现场应急处理事宜。另一种是,“应急指挥系统(常设)+各专业应急处理系统”,即政府常设一个灾害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统一领导应急救助和突发灾害处理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平时与各部门及应急事件顾问团(可以由各行业专家兼职)保持密切联系,收集信息,研究制定预案;一旦灾害发生,迅速与相关部门的专业应急处理机构共同拿出可供领导小组讨论的参考意见。还可在灾害发生时,设立应急指挥中心,与办公室合署办公,但指挥长应由政府领导担任。现在广州、上海的城市应急中心大体属于这种模式。第三种是,把上述模式结合起来,形成“应急指挥系统+综合性应急管理系统+各专业应急处理系统”的模式。不管选择何种模式,都要以快捷反应、高效运作为目标。三、还须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应急机制
城市应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应急机制建设。科学的社会公共应急机制,不但能应急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且能使公众应急行为更加自觉和有序,从而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建立和完善公共应急机制,应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应急的法治机制。经过20多年的法制改革和发展,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已有一定基础,但还远不完善,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以这次抗击非典为例,疫情暴发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疫情蔓延,中央领导亲临抗击非典一线,国家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进行规范和管理,同时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各部门也根据法律授权,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抗击非典的战斗举国展开。但是,由于非典是新发传染病,过去未曾经历,有关公共卫生紧急法律制度就凸显缺陷:一方面现行法律尚不健全,需要充实完善的地方颇多;另一方面,已有法制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到位。因此,必须建立政府应急事件处理的法律机制,提高政府应急处置能力;尤其对加大政府部门协调、组织机制落实、人财物调拨的力度等,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通过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来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明确公民在紧急状态下应当承担的相应权利和义务,使公民权利如生存权、健康权、知情权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使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的依法行使,一句话,要使应急举措遵循法制,且得到法律保障。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应急的政策机制。这是政府加强应急管理、健全应急机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减灾十年”,防灾与减灾已成为世界各国应急政策的主要内容,所以,这些年各国虽然遭受过如此多的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但世界还是保持了总体平稳。总结中国和世界应急政策的经验,有几个要点应当把握:一是要着眼于事发前的准备。俗话说“有备无患”,虽然对于难以预料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很难做到完全“无患”,但“有备”或“无备”结果大不一样。防范于未然,往往可以使灾害减缓,使重大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危害减轻,可以减少或消除因灾害、事故带来的人身、财产和经济发展的损失。在应急政策上,美国特别注重对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预防。二是要体现政府救助、社会救助和受灾者自救的相结合的原则。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应急政策主要体现为政府救助为主的原则,但中国国情不同,我们国家不仅财力有限,而且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长期以来,依靠这种伟大的精神,已经战胜和正在战胜诸如特大火灾、洪灾、地震、非典等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所以,政策原则不能丢。三是要有激励和约束力度。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对抗洪英雄、抗击非典的白衣战士,不仅大力宣传表彰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在政策上明确规定,其子女招工、参军、上学等优先录取,而对于在应急工作中有违纪行为者,都要从重从严从速查处。在这次抗非斗争中,对个别工作马虎、玩忽职守的领导干部就果断地进行了严肃处理。这种奖惩分明的政策对于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很有作用。
再次,要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应急的保障机制。“巧妇难为无未之炊”,应急工作离不开资金和物资的保障。物资也可用资金换取,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有钱。那么,受灾社区和受灾者的钱从何而来?一种方式是实施灾害保险。在美国,主要是通过联邦和州财政资助,实行全部灾害保险。在我们国家,灾害保险制度也已实行。在抗非过程中,中央明确要求保险部门把非典列入灾险范围,并迅速理赔。作为城市政府的领导者,一定要看到灾害保险对人民群众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维护灾后社会秩序的重要工作,积极组织灾害保险,以此分解国家在灾后重建中的经济压力。另一种方式是,建立政府应急基金和由政府临时增拨应急经费。采用这种办法,无论对于加强宏观控制还是对解决现场应急处理的资金困难,都比较有效。城市政府每年应从本级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充实政府应急基金,以确保应急需要,避免因政府财政乏力而给人民群众和国家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此外,还可以通过接纳社会捐助来弥补应急经费的不足。社会各界的捐助特别是企业的捐助,可以在平时通过常设机构,如应急管理机构、民政部门、慈善机构、红十字会等募集和管理,也可以在紧急事件发生时,由临时成立的专门机构动员和组织。对应急资金和物资,还要特别加强管理,要以十分严格的制度,确保这些钱物能用到“刀刃”上,及时到位,保障供给。
城市公共应急机制还包括领导机制、协调机制、督查机制、舆论机制等等,都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