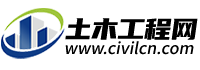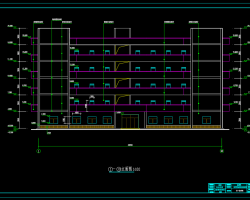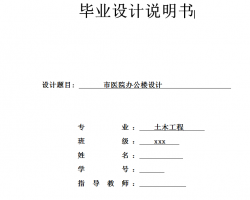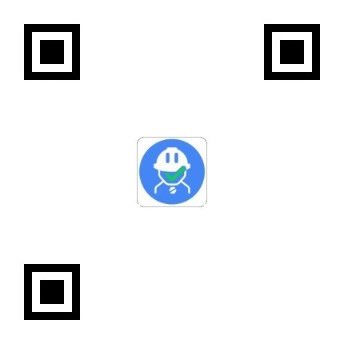摘要:在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背景影响下,形成了迥异的自然观。西方重视分离、分类,强调建筑本体和几何学特质,把时间要素脱离于建筑空间之外。而中国古代在儒道思想影响下重视空间的关系性和人与自然的连接性,在空间序列中带入时间性。而自然观的差异导致了对于建筑空间营造的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处理方式。
关键词:自然观 分离 连接 本体 关系性 时间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正文:
自然观是历史积累的人类对自然演化和存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西方自然观的形成,基于对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渐渐得到确立并作用于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发展。中国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始终与西方似乎是在各自的两条路径上不相交地独立发展。在此作用下,形成了中西方城市和建筑空间的差异。
一、中西方自然观概述
1、西方的自然观
在对待自然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指出,西方思想在两个世界之间摆动:一个是被看作自动机的世界,这是一个沉默的世界,是一个僵死而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行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人被从自然界中孤立了出来;另一个是上帝统治着宇宙的神学世界,自然界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运行的。[ 伊・ 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P38-39]古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起源之一,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自然观,把自然看作一个独立于人的对象,人与自然相对的独立性与分离就已显现。
另一方面,这样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特质。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由Idea及其模像构成的,Idea在这里可以解释成作为内在秩序、抽象性、抑或美这些客体,而模像则是承载这些客体的物理形态。因为上帝是统一的、绝对的,最趋近于上帝的形体是球体,因而球体及可被球体内切的其他几何形体则是理想的、更能趋于并反映美和客观自然的形态,我们称之为柏拉图形体。柏拉图认为Idea与主体是完全分离的,要认识Idea是很困难的,人类只能勉强通过其模像来认识它,而柏拉图形体则是能认识Idea的理想模像。[ 隈研吾:《反造型》,P73]西方Nature的概念似乎更倾向于上文所说的客体,一种绝对的秩序,一种抽象。所以也不难理解西方一贯对自然的几何性的处理,以使之更趋近于美(Idea)。而人同自然的关系,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立和驾驭,却始终存在着相对独立和分离,因此独立性和分离性也渐渐成为贯穿于西方人对待世界的思维模式。
2、中国传统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在《老子・道德经》中有根本的阐释。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世间万事万物皆可分为天、地、人、道,在这四者之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自然”居于最高位置,万事万物都应从属于它。
在这样一个法则之下,中国传统中并不视人、天、自然这三者为各自独立的范畴,而更习惯于将三者模糊在一起表述,感觉三者本就是不可分离相互统一的。与西方绝对化的理论态度相对,儒道思想都混淆着天地人伦和政治,这些特征反映了中国人认为天道、自然都可在一个完备的人身上或好的建筑上融会贯通。
另外,西方人强调个体,或者说是本体;而中国传统主张对立统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强调事物间的关系性。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古代阴阳说就揭示了以“成对”事物而非独立事物作为本体单位的观念。这也就是中西方“合创”与“独创”的差别。《道德经》说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其中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无不揭示了其中对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因此较之西方强调“本体”和“分离”的自然观下,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形态。
二、自然观差异影响下的中西方建筑空间
1、分离――连接
“分离”和“连接”是隈研吾在其著作《反造型》中提到的两个东西方自然观概念。在西方“分离”意识下,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只有严格的区分,才能表达事物的本身。而中国传统更注重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物质之间是即区分又相互渗透的、相对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重视事物的分类,很早就将建筑按照功能的不同进行建筑类型的区分,并分别赋以相应的形式;而中国传统建筑虽然也有功能上的区分,但承载这些功能的建筑形式大多并没有类型学上的差异,仅存在建筑等级的不同(如中国小到住宅大到宫殿都采用的是合院的形式)。
在城市空间中,中西方的差异性尤为明显。西方传统城市长久以来都以自然对立物的状态存在。无论是在市民城市中,还是在领主城堡中,为自然留出的空间都是鲜见的。巨大而密集的建筑物,挤出的边界分明的街道和广场,几乎看不到行道树。城堡也是凸显于山岩或旷野之中,成为周围自然的对立物。他们认为自然与人工构筑物是泾渭分明的,人类的建造是对自然的抵抗。然而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历代帝王都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秦汉直至明清,都城或皇城内无不开池凿山兴修苑囿,力图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以顺天道。
从建筑单体角度上说,“坚固、适用、美观”是西方建筑的三个基本原则,“坚固”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人类视图通过追求建筑的永恒来达到自我价值的永恒。而“永恒”所反映出的是与自然的进一步独立和分离,建筑对于处于其内部的人来说是较为封闭的以追求纯粹性。而中国传统建筑相对而言就开放得多,轻盈的结构、通透的隔断、呼吸的庭院,建筑充当人与自然沟通连接的媒介。中国古代选取“木材”这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建筑材料,这本身就蕴含了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性。中国古代自儒家起就崇尚“卑宫室”,不刻意追求建筑的永固,而是抱着与自然谦和化一的态度,才使得木结构建筑在近代西方文化渗透之前代代相传。
2、实体性――关系性
由西方的“分离”与东方的“连接”的差异性带来了对于建筑认识上相应的“实体性”与“关系性”。上文提到西方注重建筑本体,而中国传统建筑重视建筑与人、建筑与环境的对话,重视相对事物间的关系性,由此导致了中西方建筑空间处理上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呈现出的形态。
西方建筑物是独立的(甚至孤立的)、纪念碑式的、垂直发展的,且靠建筑内部所有功能房间的集中性组织来形成外部的独立而集中的形态。中国传统建筑则是所有功能房间散开,依靠连廊和庭院将其组织串联,建筑呈水平向发展,伏于大地,依山就势。故前者为“栋”,后者为“间”。“栋”是独立、分离的实体,与环境割离;“间”是将建筑化作无形融于自然,将自然带入间与间的关系之中,与人的身体发生联系。
3、时间性
柏拉图将时间剔除在形而上学之外,他的时间观被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普遍接受,认为上帝是在时间之外的。因此,在此影响下,作为追求永恒的建筑,便极力剔除时间性,而追求一种恒定的、静止的建筑观,这同时也直接导致建筑形态的实体性。
在追求“去时间性”的情况下,在人与建筑的关系中势必带入“距离”。唯有在一定距离之外,建筑以完整二维立面展现,建筑才是稳定、静止的。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透视法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时间观和建筑观,将一定距离之外人所见建筑的画面转移到画布上。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建筑恰恰是追求时间性的。由于建筑的形态并非独立集中的单一形体,而是伴随着空间序列的建筑关系合集,人对建筑的体验不是瞬间的整体的,而是伴随着人的进入和与建筑的互动发生感知,进而认识建筑和空间,如传统四合院、园林以及宫殿或坛庙。所以中国传统建筑也没有“立面”的概念,其建造也并不依照既有的二维投影图。若剔除时间性,对建筑的感知便无法完成。
4、对称――对仗
西方的绝对性思想体现在空间上对应的是对称,重要的官方建筑如宫殿、教堂或皇家园林,无不遵循轴线左右的严格对称。而在中国古代的空间处理上,尤其是法统空间,受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观念的影响,虽也强调严谨的轴线,但更强调轴线两边的对仗关系而不是表象上的对称。如《周礼・考工记》中提到都城规划依循的“左祖右社”等,包括明清紫荆城的规划布局清晰明确的轴线左右是严谨的空间对仗而不是形态对称。